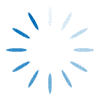吉原的夜,从来都是由金铃般的娇笑、缠绵的叁味线、和醉客的喧哗编织而成。而这一夜,樱屋的喧嚣更胜往常,声浪如潮水般拍打着每一根梁柱,每一扇纸门。
叫价声、惊叹声、女将因激动而拔高的唱价声,混合着浓烈的酒气与脂粉香气,从楼下大厅阵阵传来,清晰得仿佛就在耳畔。
清原绫端坐在镜前,宛如一尊被精心妆点的人偶。镜中映出的容颜,美得令人窒息,却也陌生得让她心悸。
脸上敷着最上等的白粉,细腻如瓷,不见半分肌理。唇点得极小,却红得刺目,宛若雪地中一滴凝固的血,也像商品上最显眼的价签。
高耸的发髻间插满玳瑁梳与金箔花簪,沉甸甸地压着她纤细的颈。身上层迭的裾拖是朝雾姐姐昔日的荣光,金线绣出的凤凰振翅欲飞,此刻却只让她感到这是一副华丽而冰冷的枷锁。
今夜,是她的“扬名之夜”。
吉原的规矩如此,这是一个游女真正开始用身体丈量苦难、以血肉偿还那永无止境的债务的开端。
她的命运,在那些醉醺醺、欲望横流的呐喊声中,被一次次刷新,直至定格。
她静静地听着,面色无波,仿佛置身事外。唯有藏在宽大袖中的手指,冰凉得没有一丝温度,微微蜷缩着。胃里像是塞了一块坚硬的石头,沉甸甸地往下坠,带来一阵阵生理性的恶心。
从八年前那个雪夜起,她就知道会有这一刻。理智冰冷地告诉她,这是无法逃脱的宿命,是活下去必须支付的代价。
她甚至早已在脑中预演过无数遍——或许会是一个脑满肠肥的富商,或许会是一个性情暴虐的武士,也或许是一个短暂的温柔过后便将她弃如敝履的贵族。
她告诉自己,要忍耐,要像朝雾姐姐教导的那样,将灵魂抽离,只留下一具美丽的空壳。
可当楼下的竞价声浪越来越高,几乎要掀翻屋顶时,那股冰冷的、深入骨髓的绝望还是丝丝缕缕地从心底最深处渗出来,缠绕住她的四肢百骸,让她几乎无法呼吸。
她不是一件没有知觉的商品。她是清原绫,也曾读诗书、知廉耻。
就在这时,一个异常清晰、冷静的声音,如同利刃般劈开了所有的嘈杂,报出了一个让整个大厅瞬间陷入死寂的数字。
是藤堂朔弥的声音。
没有激昂,没有炫耀,平静得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既定的事实。然而那个数字本身,却如同惊雷,炸响在每个人的耳边。那是足以令人瞠目结舌、甚至买下半条街铺面的天价。压倒性的。毫无悬念。
藤堂大人------!!
女将狂喜到近乎变调的尖叫声,穿透了楼板,也像一根针,猛地刺入绫的心脏。
她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,又在下一秒疯狂地奔涌起来,冲撞得耳膜嗡嗡作响。
是他……竟然是他。
一股难以言喻的、近乎可耻的庆幸,如同温暖的潮水,瞬间淹没了先前那冰冷的绝望。不必再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、或许会粗暴对待她的男人。至少……是他。
然而,这庆幸只持续了短短一瞬,便被更汹涌的难堪与羞耻所取代。她最不堪、最被迫展示于人前的时刻,竟是由他,这个曾在她心中留下复杂印记的男人,用巨额的金钱买下。
他看得一清二楚,她是如何像一件货物般被陈列、被估价、被争夺。这认知让她恨不能立时化作一缕青烟,消散在这令人窒息的空气里。
纸门被无声地拉开,又轻轻合上。
沉重的、不疾不徐的脚步声停在她身后。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冷冽的松香,夹杂着淡淡的酒气,那是属于他的气息。
绫没有回头。她只是望着镜中那个浓墨重彩的玩偶,看着镜中映出的、那个穿着深色吴服的高大身影。他站在那里,如同沉默的山峦,投下的阴影几乎将她完全笼罩。
他来了。用这吉原前所未见的天价,买下了她的初夜,成为了她名义上的相公——最高级的恩客。
结束了。她心里一片死寂的空白,等待着预料中的触碰,或许还有带着酒气的、审视的目光。她甚至微微闭上了眼睛,将所有的情绪——庆幸、难堪、恐惧、茫然——都死死压进那片空白之下,身体僵硬得像一块被冰雪封冻的木头。
预想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房间里只有烛火哔剥的轻响,和她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。
良久,她听见他的声音,平静得像窗外沉沉的夜色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:为我跳一支舞吧。
绫猛地睁开眼,从镜子里看向他,瞳孔因震惊而微微收缩,怀疑自己是否因过度紧张而产生了幻听。
朔弥的目光透过镜子与她对视,深邃的眼眸里映着跳动的烛光,重复了一遍,清晰而确定:就跳《白拍子》。
震惊像冰冷的泉水般浇遍全身,瞬间冲散了那层麻木的绝望。跳舞?在初夜?在她已经做好了献出一切准备的时刻?他花了足以让整个吉原为之侧目的巨额金钱,仅仅是为了看她跳一支舞?
荒谬。不可思议。这完全超出了她所有的预想和认知。
她下意识地转过头,第一次真正地、毫无遮蔽地看向他。他的脸上没有戏谑,没有嘲弄,甚至没有常见的欲望。
那双总是难以看透的眼睛里,此刻依旧翻滚着她无法理解的复杂情绪——有一丝探究,一丝审视,或许……还有一丝极淡的、被她舞蹈吸引后的期待?这不是玩笑,也不是欲擒故纵的把戏。
一种极其细微的、几乎不敢辨认的情绪,从冰冷的心底裂缝里小心翼翼地钻出来——那是一丝……被尊重的奇异感觉?虽然这尊重是以如此昂贵和古怪的方式呈现。
她没有问为什么。在吉原,恩客的要求就是命令。尤其是刚刚一掷千金的恩客。
是。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地回答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她起身,走到房间一角的屏风后。繁重的头饰和层迭的外衣被一件件卸下,那些华丽的枷锁被暂时解除,她感到一阵短暂的、近乎奢侈的轻松。
她换上了一套素白的舞衣,没有任何纹饰,宽大的袖子和裤腿,干净得像一片初雪。
脸上浓厚的白粉和嫣红的唇,在这极致的素净下显得格外突兀,但那反而凸显了她眼底深处无法被完全掩盖的清澈与挣扎。
她走到房间中央。烛光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,摇曳地投在墙壁上,像一个孤独的、即将起舞的魂灵。
没有音乐。吉原的夜晚从不缺少叁味线和太鼓的喧嚣,但从隔壁房间隐约传来的、软绵绵的靡靡之音,与此刻室内的绝对寂静形成了诡异而令人心慌的对比。
她深吸一口气,闭上了眼睛,试图将所有的杂念摒除。
再睁开时,眼神已经变了。不再是那个惶恐不安的新造,也不再是那个认命待宰的游女。仿佛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,在这一刻苏醒了过来。
她抬手,起势。身体的记忆被瞬间唤醒,那是刻入骨血里的东西,是家族未败落前,母亲悄悄请人教导的、不属于吉原这座牢笼的风雅。
白色的衣袖如流云般挥出,带起微弱的风,拂动了案几上的一豆烛火,光影随之剧烈晃动。
起初是缓慢的,带着试探般的凝滞,仿佛在摸索着被遗忘的感觉。随即,节奏逐渐加快,越来越流畅,越来越激烈。她旋转,腾挪,扬袖,顿足。
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充满内在的力量,柔美中带着韧劲,完全不像她平日表现出的那般娇弱。
没有音乐,但她的舞步就是节拍,她的呼吸就是旋律。那素白的身影在昏黄的烛光下仿佛一团燃烧的、冰冷的火焰。
她跳的不是取悦男人的艳舞。她把八年来所有无法言说的一切,都融进了这舞姿里。
被灭门的那一个雪夜,老仆忠藏最后的嘱托,初入吉原时的恐惧与绝望,朝雾姐姐戒尺下的疼痛与深夜偷偷的抚慰,对高墙外天空那一瞥的向往,那些刻苦磨练的茶道、叁味线、和歌……
还有,还有眼前这个男人带来的——小巷中的出手相救,棋盘对面的无声交锋,那些新奇却冰冷的礼物,窗外摘下的樱花枝,以及此刻这完全出乎意料的、用天价换来的“一支舞”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混乱……
所有压抑的情感、所有无法言说的悲恸、所有在淬炼中生长出的坚韧、所有对自由的渴望,尽数化为舞蹈。
她的身体成了表达的武器,悲怆而空灵,绝美而破碎。烛光投下的影子疯狂舞动,似在与无形命运抗争,又像在进行一场孤独祭奠。
有一瞬,在一个急速的旋转后,她的目光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他的。他依旧坐在那里,姿势未变,但眼神深得像潭,里面翻涌着她看不懂的暗流。
那一刹那,她动作几不可察地一滞,眼中闪过一丝动摇,旋即又没入更深的舞意之中。
她跳得忘我,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以一个近乎决绝的、俯身于地的姿态结束了舞蹈。汗水浸湿了额发,粘在涂满白粉的皮肤上。胸口剧烈地起伏着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痛感。
她伏在地上,不敢抬头,更不敢看他的反应。极致的宣泄后,是巨大的空虚和脱力感,几乎将她彻底吞没。
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只剩下她无法抑制的、急促的喘息声,以及烛芯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。
时间仿佛停滞了。
不知过了多久,沉稳的脚步声靠近。一件还残留着体温的、触感极其细腻华贵的墨色羽织外袍,带着一股冷冽的、干净的松木香气,轻轻地、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,披在了她因剧烈喘息而不断颤抖的、只穿着单薄舞衣的肩上。
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,那是一个宣告。宣告着所有权,宣告着从这一刻起,她被标记,被归属。
他低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,依旧听不出什么明显的情绪,却带着一种天然的命令感,清晰地落入她的耳中:以后,你的时间大多属于我。
然后,脚步声再次响起,走向门口。
纸门被轻轻拉开,外面喧嚣的声浪瞬间涌入,又随着纸门的合上而被彻底隔绝。
他就这样走了。
没有触碰,没有强迫,没有留宿。
绫久久地跪伏在原地,羽织上属于他的气息和温度丝丝缕缕地包裹着她,带来一种奇异而矛盾的感受。
肩上华袍的重量清晰无比,提醒着她被买下的事实;而他离去时那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关门声,却又像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体贴。
紧张和绝望褪去后,是巨大的茫然和难以置信。震惊于他那难以理解的举动,更震惊于自己内心汹涌而出的、超越恐惧与利用的好奇,与那一丝微弱却无法忽视的感激。
他看到了什么?在那支舞里?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?这真的只是更高明的驯服手段吗?
理智仍在尖声提醒,提醒她吉原里从无例外,一切都是明码标价。这或许只是更高明的手段,是欲擒故纵。
可那一刻被真正“看见”的震撼,那一刻被当作一个有着复杂内心的“人”而非仅仅是一件美丽“物品”来对待的瞬间,却如石入深潭,涟漪再难平息。
她下意识地拢紧了肩上那件过于宽大的、属于男性的羽织,将自己更深地埋进那片带着冷冽松香的黑暗里。
第一次,对这个名为藤堂朔弥的男人,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、无法忽视的动摇与探究欲。
而此刻,已然行走在吉原绚烂灯火下的藤堂朔弥,眼前挥之不去的,仍是那抹在烛光下激烈燃烧、仿佛要将自身也焚尽的素白身影。
那舞蹈里的悲怆与不甘,那份深藏的坚韧与骄傲,像一把精准而锋利的钥匙,猝不及防地撬动了他内心某个早已冰封的、不为人知的角落。
披上外袍,是所有权的宣告;或许,连他自己都未曾全然意识到,那更是一个下意识的、想要为她隔绝窗外一切窥探与污秽的保护姿态。
一种陌生的、久违的柔软情绪,在他冷硬的心房深处,悄然滋生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